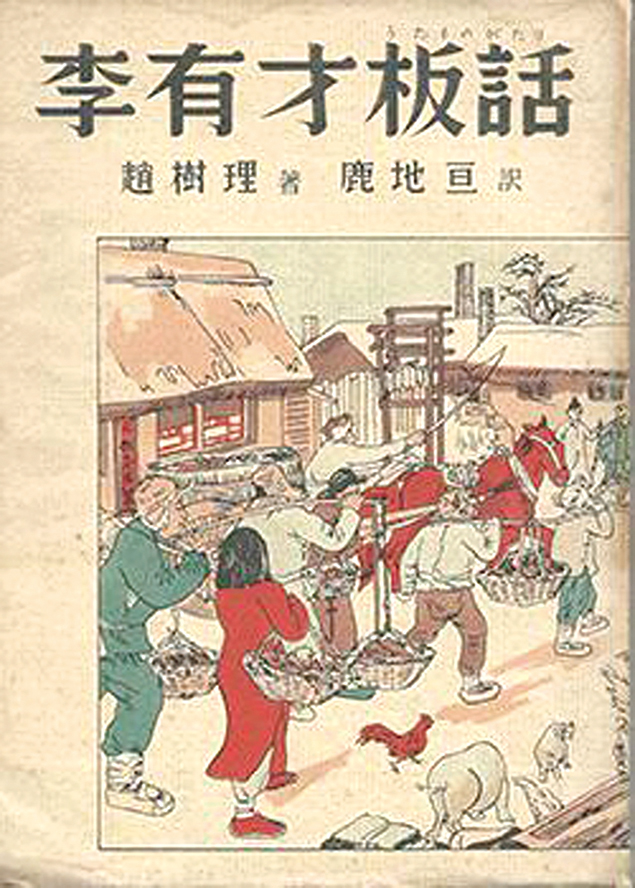
赵树理作品《李有才板话》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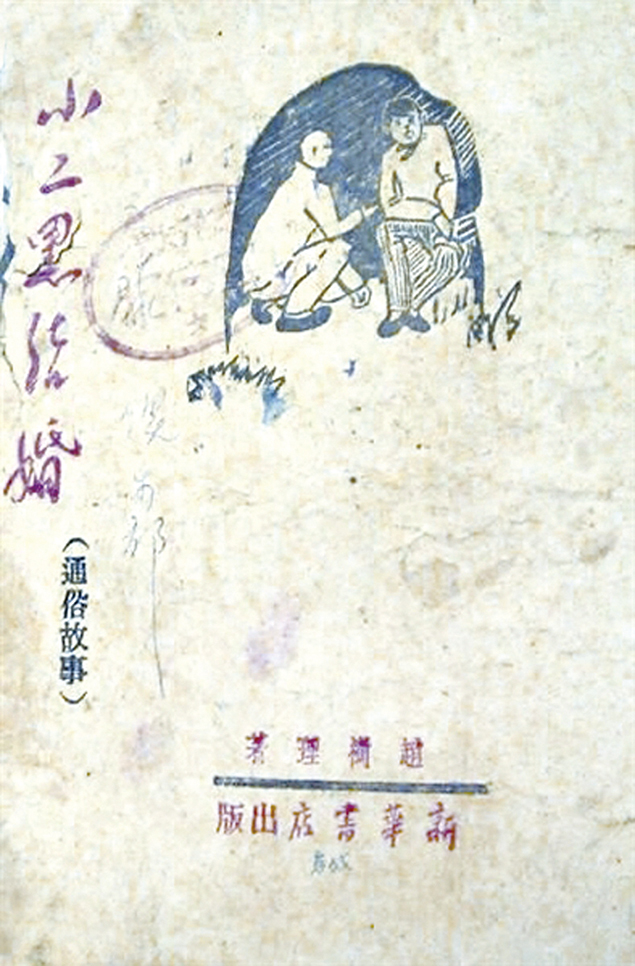
赵树理作品《小二黑结婚》(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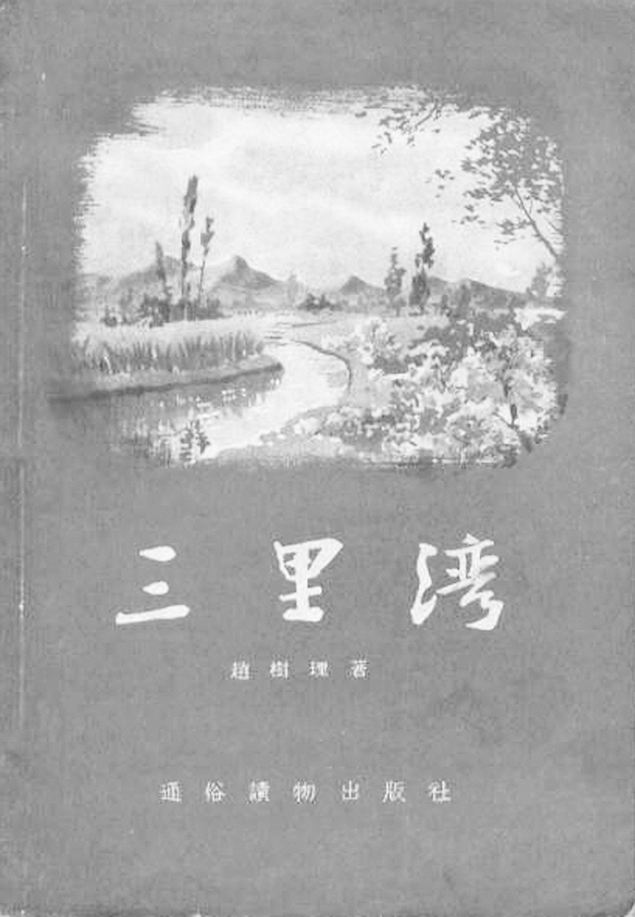
赵树理作品《三里湾》(资料图片)
鲁迅的未庄、周立波的清溪、柳青的蛤蟆滩、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香椿街,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以一个具体地理空间为基础展开的书写,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
书中的人与事
前两天,尉迟村刘军善书记和我说,他做过精确的测试,从嘉峰到望川,1500米,三华里,沁河边真正的三里湾,湾头嘉丰,湾尾望川,尉迟在湾的中心。有人说《三里湾》的素材是平顺县的川底村,川底村现已改为三里湾村,有人说《三里湾》写的是武乡县监漳村,现在监漳最大的农业经济合作社就叫三里湾合作社。这些地方确实是赵树理在写《三里湾》前下乡工作和调研的所在。川底和监漳,村前都有一条河,有河就有湾,但是赵树理笔下的三里湾在哪里?大家去认真读一遍《三里湾》,写得最真实、最可爱也是最贴切的地方一定是他的家乡尉迟村这个沁河边的三里湾。因为只有这个三里湾是他儿时的记忆,是长在他的心里的,是他的根和魂。特别是以小说《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的主题歌:“三里湾,三里湾,对着水,靠着山,青枝绿叶上下滩。自从有了农业社,又治水,又治山,人定胜过天。”这支歌是赵树理编词,大家想想看,这是不是尉迟村最真实的写照?
他1943年写的《李有才板话》,是在左权县麻田乡峧沟村李家岩自然村写的,那里在抗战时期曾是太行五行署的驻地,赵树理在1939年春与魏建、齐云夫妇一起从阳城调到五行署,曾在那里工作。有一个真名实姓的李有才原形。2018年10月我们到那里采风,见到了李有才的儿子李德胜,那个地方是石头山,李有才的房子是石块干垒的。看赵树理书中怎样写:“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瓮,锅、匙、碗、碟,靠后墙摆着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村里人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给他送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那么高,打了个半截套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像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像石菩萨的神龛,回头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里的小饭铺。”这样的“三看三变”的土窑洞哪里有?离尉迟二华里的大骡沟,五华里的赵树理的前岳母家牛角岭,前两天我们到嘉峰镇前岭村寻访赵树理写的《前岭人》何洪义的故居也是这样的土窑洞,并且格局有提升,窑洞上下两层楼。
我们曾走访他上长治师范前任小学教员的野鹿、板掌。野鹿的大庙在村后依山的一个高高的土堆上,庙里虽然戏台坍塌得只剩下一根石柱子,但正殿和两边的偏殿还在,古建筑历经沧桑,风骨犹存。站在庙院的荒草丛中,就似乎回到了《李家庄的变迁》中“血染龙王庙”的故事现场。
他1947年写的《王二和与刘继圣》中的王二和就是他自己的影子,他在少年时上私塾常被村长家的孩子欺负。王二和在三角坪和一堆放牛的孩子扮成罗成和张飞挥舞着桃树枝和高粱秆演打仗的戏,这正是沁河流域流传甚广的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上党梆子;下到河里玩“水汪冲旱汪”的游戏,这也是上世纪初尉迟一带儿童在玉沟河边玩的最有挑战性的游戏。包括他在上世纪30年代写的《有个人》《金字》《盘龙峪》,都少不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映的是沁河流域的民情民俗民风。在《打倒汉奸》中,黑蛋娘说黑蛋:“人家都是见缝就钻,他不会看风驶船。念书念了十年,他爹也快把地卖完,谁知他毕了业家也不回,事也不干。”这说的就是赵树理从长治师范逃进深山四处流浪的情景。
赵树理自己也讲过多次:“《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兴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区的旧渣滓,《李有才板话》中老字辈和小字辈的人物就是我的邻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庄的变迁》中六姥爷的‘八当十’高利贷逼得破了产的人,同书中阎锡山的四十八师留守处,就是我当年在太原的寓所,同书中‘血染龙王庙’之类的场合,染了我好多同事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他还讲:“《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我们村子里有这样的人,别的村子里也有这样的人。”
李士德1979年5月在尉迟采访村上老人吕培信,吕说:“‘不宜栽种’讲的就是他爷爷赵东方的故事,赵树理写小说,有的人物就是我们村的人。像张存财,好唱个小调,说个快板,为人正义,赵树理在书中把他改为‘李有才’。‘福贵’其实是‘富贵’,是赵树理本家的一位兄弟。‘三仙姑’也是他本家的一位嫂子。”
李士德1981年9月在尉迟采访村上老人李育秀,李说:“‘三仙姑’的雏形也有,她是赵树理本家的一位嫂子,农村妇女一般都穿土布衣服,她却每天涂脂抹粉,穿红戴绿,打扮得花枝招展。张存财送她外号‘夜来香’,一见到她就对人说,‘驴粪蛋上下霜’,讥笑她老来俏,满面涂粉,也抹不平那黑脸上的皱纹。”
他在1959年写的《新食堂里忆故人》,更是句句情深意切:“我的故乡,在太行山南端的西边。我不但在那地方生长、上学,而且直到全国大解放以前,都在那个山区工作。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关系,我在解放以后虽然离开了那里,但一有机会,总想回去看看。我每次回去,总能碰到一些新鲜的事物。我所写的小说,大部分取材于这个地区。”
他在写了村里新建的食堂之后,就写道,“慢慢联想起好多故人来”,于是从“南院门口”的各轮、“窨头上”的栓成、随成,南边冯家的富贵,“东头院”吕家兄弟,大核桃树下古石窑住着河南遭水灾逃荒到这里的人,并写道:“我写《李有才板话》中的‘老字辈’的人,好多取材于这里。”他怀念故人“老字辈”的人,更期盼新人“小字辈”的人生活得更好,他在结尾时说:“我以两只手在他们头上摸来摸去,又指着每个问他们的名字。嘴快的指着每一个介绍给我他叫小什么,他叫小什么,可是我连一个也没有记住,每一个名字前边只记了个‘小’字。我觉着这也可以说是些“小字辈”人物吧,不过比我在《李有才板话》中写的那些‘小字辈’人物幸福多了。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懂得什么叫‘逃荒’。”他对家乡子弟血浓于水的深情读起来令人心动。
浓浓的家乡情
今年春天的疫情给了我们闭门读书苦心钻研的机会,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占平由此爆出了“山药蛋派”作家“家园情结”的新观点。他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始终坚持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在表现北方农村的生活状态和农民的思想情感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文学的表现手法上也独树一帜,成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最受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山药蛋派’作家值得读者记忆值得后辈作家学习,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们有着强烈的家园情结。”我认为,他这个家园情结的观点提得好,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正在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转型蹚路的紧要关头,它对于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充分激发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对于我们资源型地区走出资源依赖的困境、以绿水青山开展文化生态康养旅游、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都有着实际意义。
“山药蛋派”作家在太行山和吕梁山根据地迷恋上文学创作,小有成就后,绝大多数都离开故土,走向了外面的世界,赵树理、马烽去了北京,西戎、胡正去了四川,孙谦去了东北。他们当时都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黄土地外的文明和大城市的繁华,对他们有着强烈的诱惑,他们幻想着城市生活的丰富和潇洒。然而,过了几年后,他们却先后又都回到了太行山和吕梁山下,回到了沁河、汾水岸边。在外面的数年中,他们当然没有放弃文学创作,发表过一些不错的作品,那么,他们为何要重返故土呢?赵树理说,“我是在农村中长大的,而且在参加革命以前,家庭是个下降的中农,因此摸得着农民的底,这是我自以为幸的先天条件。”“我已写出的作品,其题材全部是农村的事。我和我写的那些人物,到田地里做活在一块作,休息同在一株树下休息,吃饭同在一个广场吃饭,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我既然这样了解他们,自然就能描写他们。”“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后,我也曾下过一次工厂,但试验了一个月,觉得路子太生,又想折回来走农村的熟路。”马烽也讲:“我在北京待了将近七年,深深感到住在北京城里写山西农村生活,不是个办法。‘京华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后来就下决心卷上铺盖搬回了山西。”
他们回到山西以后,在家乡的土地上,很快便寻找到了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价值,用全部身心去感应这块土地上的痛苦与喜悦、喧哗与骚动,独特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和生活氛围,犹如浓得化不开的情愫,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理想港口。赵树理在谈到他这方面的感受时说:“当我在一九五一年重新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机关驻扎的一个山村的时候,庄稼长得还像当年那样青绿,乡土饭吃起来还是那样的乡土风味,只是人们的精神比以往活跃得多——因为我们有了中央政府,老乡们都以胜利者的姿态欢迎我这个回来的老熟人。”“和这种老战友共事有个痛快劲儿,那就是他们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养成了些不计个人得失的忘我精神。他们虽然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但也是些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们遇上了新鲜事物,不但顾虑不多,并且兴趣颇大。”回到家乡那种热烈、亲切、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他们如鱼得水,手中的笔顺畅起来,作品纷纷问世,进入了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赵树理写出了《三里湾》、马烽写出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西戎写出了《赖大嫂》、孙谦写出了《伤疤的故事》、胡正写出了《汾水长流》。他们认定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是自己写作的根本之路,因而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风格,坚持深切关注农民命运、关注农村发展,再加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富有个性、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大作家。
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往往都带着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高度的鲜明的典型性。这些人物几乎每一个“都包含一部分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都包含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出现过无数次痛苦和欢乐的遗物”。比如,赵树理多篇小说中都有农村的“婆婆”形象。《孟祥英翻身》中虐待孟祥英,叫干活又不给饭吃,唆使儿子往死里打孟祥英,甚至要把孟祥英卖掉的那位“婆婆”;《登记》中教唆儿子用老木匠打她的锯梁子打儿媳妇,使其屈服于包办婚姻的“婆婆”;《三里湾》里的“常有理”,对不服从自己意志的儿媳妇“菊英”,推了半天磨,晌午只给面汤喝,不给面条吃;《传家宝》里的李成娘对儿媳妇金桂热心于社会、生产活动,不事女红,半拉眼珠看不惯,等等。这些女人,都带有沉重的被几千年封建礼教压迫、扭曲的心灵创伤。赵树理对这些农村“婆婆”简直太熟悉了。他爷爷“年轻时……曾连续娶过几房妻子,都因母亲虐待,而相继夭亡”。他自幼与这些“婆婆”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对她们的言谈举止,气质神态,烂熟于心。一旦受到启发,产生创作欲望,信手拈来,便会点石成金,跃然纸上。
再比如,《李有才板话》采用平话体的叙述语言,写人叙事,除用口语俗白,还不时夹以押韵的快板诗,语言朗朗上口,生动异常。这是对地方戏曲和曲艺等民间艺术模式的推陈出新,也是赵树理家乡文化生活积淀的外化反映。晋城、沁水一带,戏曲、曲艺艺术流布很广,“圪溜嘴”(快板诗)在乡间十分流行。赵树理从小就是戏迷,邻村凡有夜戏,他必到场,到场必听到端鼓散场。他又是上党戏的行家里手,所以,民间戏曲、曲艺的叙事话语已注入他的血脉,一旦创作,这些流淌于他血脉中的艺术情结,自然会涌注笔端,放射出熠熠的光彩。
从“山药蛋派”作家的家园情结,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当作家离开故土,到了外面的世界以后,有了反观本土文化的机会,不同文化的碰撞,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灵落差;地域的位移,造成他们难以将创作心态调整到最佳状态的困惑。在远异于家乡本土的异质文化中,他们不能不感到文化的失落感,无时不怀念起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人,文化基因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精神事物的内在功力,对他们的潜移默化、滴水穿石,铸成了他们的根和魂。因而,他们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后,才能爆发出创作激情,写出优秀作品。由此看到,作家的家园情结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也成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经验。
不变的赤子心
赵树理是一位在创作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作家。在他的故事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位作家对于人民、特别是家乡人民的真挚热爱和忠诚。这种对人民的真挚情感是一位作家与生俱来的品德,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践中对写作者自我品性的不断陶冶与修炼。这种情感关系到一个作家创作的态度,同时也关系到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在赵树理的作品中,我们读到的正是作为文艺创作源头活水的人民,而作为文学原料的丰富矿藏的家乡人民的生活,始终是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赵树理故事中以家乡人为雏形的主人公,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小二黑、小芹、李有才、孟祥英、庞如林,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铁锁、冷元、王二和、软英、金桂,新中国成立后的艾艾、小晚、玉生、灵芝、潘永福、何洪义,特别是有着绰号的二诸葛、三仙姑,小飞蛾、田寡妇,糊涂涂、万宝全,常有理、惹不起,吃不饱、小腿疼,他们在赵树理的笔下,都焕发出人的光彩,他们有血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挣扎、有苦恼,更有不如意和困难,但是他们都以人的精神战胜了那些现在看来也许是微小而当时是强大的困难,他们跃然纸上的一个个生动鲜活的面孔,也从来不是单一化脸谱化的,他们的生活都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就是这样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他讲述的小二黑、小芹们的故事,在今天读来仍然非常鲜活,他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人物仍然具有其他同时代作家不可比的来自民间的动人魅力,在他笔下,“‘人民’不再是五四时期需要被启蒙的大众,而是历史的、能动的主体”,这一主体的发现,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人民放在文艺创作的主体地位上的指导与引领有关,同时也更与一个生于农村、了解农民、热爱农民、发自内心对农民命运、利益关心,愿意热情书写农民并给农民看的作家的自觉意识不无关联。今天我们要了解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太行山区的人民生活,了解当时晋东南老百姓的生产劳动、婚丧嫁娶,了解历史中的无数个小二黑、孟祥英、李有才、潘永福这些具体的农民的面容、人民的理想,便不能绕过赵树理的小说。中国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铁凝讲:“赵树理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是机械地、生硬地照出,而是力求照出人的生长性更准确地说是农民的成长性。人的成长、人的解放、人的觉醒在里面,“新的人物新的世界”都在里面,这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以激情烛照现实、以进取歌唱新生的解放区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理想主义气象。这种气象同样不是理想化的拔高,而是作家对现实农民心理状况的真实反映。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扬才感叹,“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创造积极人物的典型,是我们文艺创作上的一个伟大而困难的任务”,“积极人物”的诞生,很大程度取决于作家的积极心态和在这心态下的积极发现。对于现实与人物典型,显然赵树理不是将之作为“任务”去完成的,周扬在1946年8月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中高度肯定,赵树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思想,写农民生活的作家,并于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于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再次评价,“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铁凝讲:“何以赵树理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不但来自农民,而且始终不脱离农民,不背弃农民。他了解农民,热爱农民,他是农民的一分子,他笔下的农民有着地道的农民特质,他讲述的是真正属于农民的心灵故事。农民的所思所想、所行所为,在他的文字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赵树理曾言及他与农村的关系是“母子一样的”,“离得时间久了,就有些牵肠挂肚,坐卧不宁,眼不明,手不灵,老怕说的写的离开了农民的心气儿”;他言及与生活的关系时讲,“要真正深入生活,做局外人是不行的。只有当了局中人,才能说是过来人,才能写好作品”。
家乡的故事,是赵树理创作的魅力所在。而有魅力的故事的取得没有捷径,仍然要靠与故事中的人物心贴心的书写,故事中的人物从哪里来,仍是要靠在他们成为人物之前,作家对他们生活的深切的体察,对他们命运的真切的关注,对他们情感的真挚的同情,对他们成长的由衷的欣喜,如果撤掉了这些,我们的文学只会是苍白无力,更谈不上血肉丰满,气血贯通。如何能够做到气血充盈,血肉丰满,也没有捷径,只有真真正正地脚踩坚实的大地,和人民融在一起,血肉相连,心心相印。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对于作家来说,扎根人民,是为了写好人民,而能够写好人民,其根本还在于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写作的出发点。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人民才会认可,才会爱看,才会喜欢。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并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他进一步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
时代要求与人民心声,始终装在赵树理心里,如果我们熟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讲故事的方式,不是将他自己放在前台,而是永远让他的人物——农民站在舞台的中心位置。这种让人物自己出场讲自己故事的口述方式,并不是赵树理的创新,在中国古典传统文学中我们每每与其相遇,赵树理其实是接过了这种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过多受到欧化句式或翻译语言影响之后有所断裂的传统,于此我们看到了他的口语化、短句子。赵树理常说:“写作品的人在动手写每一个作品之前,就先得想到写给哪些人读,然后再确定写法。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照顾传统的目的仍是为了使我所希望的读者层乐于读我写的东西。”形式问题从来不仅仅就是形式问题。文学作品看似是语言问题的其实也包裹着一颗心,使用这种平白易懂的语言,对应于百姓自己讲出的故事,而让老百姓自己也看得懂,看得津津有味。如果没有这样的善意和情怀,热爱说唱艺术民间传承的赵树理不会成为人民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不同于其他作家对家乡人民的情感仅仅停留在作品中,而在于他更多的爱家乡、帮家乡、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1979年5月27日李士德在尉迟采访关联中,关讲:“老赵就是太实在,太死心眼,信奉什么,一条道跑到黑。他想把家乡尉迟建设好,就把女儿广建也打发到家乡工作。尉迟的苹果、梨树、山楂,都是他从外地弄来的。帮助队里修水库、开水渠、买锅驼机,连大队的缝纫机和钟表都是他从北京买好送回来的。平时在街上碰到一块大石头也要搬开,遇上个小孩流鼻涕,也要跑过去给擦擦,有时弄得人莫名其妙。”
这就是赵树理,他对农村、他对农民、他对家乡有一颗不变的赤子心,就是要“一条道跑到黑”,无私无畏,无怨无悔。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他竟然将自己最钟爱的女儿从北京送回了家乡尉迟务农。1957年9月14日他给女儿赵广建写信,提出“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信中写道:“当时我说你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你不服气,现在我想你应该能够认识这一点吧!你有两个小小包袱,一个是高中生,另一个是干部子弟。从旧社会传来一些社会职业评价,认为读了书当了干部就应该高人一等,认为参加生产和服务业的人是干粗活的人、俗人。这种与社会主义极不相容的旧观点,偷偷地流传到很多学生和干部子弟的头脑中,而你不幸也是接受了这种坏遗产的人。”“我相信你在这几个月农村工作中认识了好多劳动人民,懂得了一些生产中的事情,而在感情方面也应该更向劳动人民靠近了一些,但我以为应该进一步在一个社里落户,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只有真正参加了生产,凭工分过日子,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前进,才能深刻体会到生产中任何问题都与自己有直接关系——即与广大群众有直接关系。只要你在生产中真有建树,你是会感到生产本身就有快乐的。”
赵树理像农民一样,从来不记日记,也不爱写信,这样的长信更是罕见。1954年去中南区慰问解放军时,他曾寄回一封家信,可是女儿赵广建拆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一张信纸也没有,经过仔细研究,才发现信封的背面有他说明平安的八个字。这封长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父亲面前,赵广建常常是个任性的大孩子。接到信后,她却跑到太谷县去,准备结婚了。说来凑巧,她的一个在《山西日报》工作的老同学也在那里,无意中发现了这封信,他凭着新闻记者的敏锐目光,一眼就看到了它的价值,便征得这对父女的同意,给它加上《愿你做一个劳动者》的标题,发表在1957年11月11日的《山西日报》上,紧接着《人民日报》和各省市的报纸相继转载,标题改为更贴切的《愿你当一位有文化的青年社员》。结果,她在婚后的第二天,就毅然决然地打点行装,回尉迟老家落户。因此,人们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也“分量最重”——几乎全是锄头、镰刀之类的生产工具。后来这封信选入了中学课本。
大家想象一下,1957年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今天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电气路、吃穿住行,城乡差距大大缩小,但即使是这样,我们扪心自问,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回农村吗?
这就是赵树理,他才是我们今天讲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优秀的共产党员。
中国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伟大变革,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此,我们怀念赵树理,就是要继承他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的文学信念,沿着他终其一生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而愤然前行!
